编者按:由于我国刑法对一般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量刑上差异很大。同样诈骗五十万的金额,如果被定诈骗罪,不考虑情节,量刑可能在十年以上(各地标准有所不同),而被判处合同诈骗罪,量刑多在五年以下。由于两者如此悬殊,律师在辩护时,总是尽可能往合同诈骗方向去辩护。辩护律师请注意:有合同是不是一定会被定为合同诈骗?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是否就一定不能构成合同诈骗?本文提供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
【案例一】虽签订合同,但只是以此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定诈骗罪
基本案情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一个“辽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号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给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将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宜章介绍给王贺军。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张发两次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杨宜章等人见面,因此,杨宜章等人对王贺军深信不疑。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 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九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宣判后,王贺军以只在第一次骗了杨宜章30万元,后来拿的杨宜章的钱以及王惠明的20万元、王小岱的11万元是借,不是骗,并还了王小岱5万元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和能揽到工程项目的事实,以许诺给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巨大,原审将王贺军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不当。王贺军上诉提出其行为是借不是骗的上诉理由,经查,王贺军的多次供述及杨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陈述均证明,王贺军一开始即虚构身份,以许诺介绍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承包合同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向各被害人诈取钱财,并予以挥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另外,王小岱陈述王贺军没有还给他钱,王贺军也不能提供还钱的证据,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王贺军诈骗了杨宜章人民币72万元,但杨宜章陈述其被王贺军骗了70万元,故本院只认定王贺军诈骗杨宜章7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王贺军的上诉,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上诉人王贺军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七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二、主要问题
以许诺让他人承揽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王贺军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贺军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虚假的工程承揽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在合同签订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王贺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一)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从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但是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出发,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立法设立该罪以专惩此类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同为诈骗类侵财犯罪,两罪在构成要件上的共性特征以及具有的法条竞合关系使得如何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这也是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分歧意见的原因。我们认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其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签订是指自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同时,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全案事实,本案中被告人王贺军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执笔: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黄 燕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王志辉)
选自《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
【案例二】虽没有签订合同,但其骗取钱财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定合同诈骗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德明,男,34岁,初中文化。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1年9月30日被逮捕。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宋德明犯合同诈骗罪,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宋德明对基本指控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宋德明与被害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宋德明不是合同当事人;被告人宋德明非法占有了哪些药品不清且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不能证明康恩贝公司丢失药品的数量和种类;认定数额特别巨大不当,应宣告被告人宋德明无罪。
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11月30日,从事包装服务业务的被告人宋德明接受浙江康恩贝集团医药销售公司(以下称康恩贝公司)工作人员的委托,为该公司在沈阳火车站发运药品。当日,被告人宋德明与该公司就代办运输、劳务费用、履行方式等具体内容达成口头协议。次日,被告人宋德明在康恩贝公司人员的陪同下,将首批应发运的药品从康恩贝公司药品仓库拉到沈阳火车站货场,装入集装箱并加锁。待康恩贝公司人员走后,宋将钥匙交给李某(搬运工)并指使李某将该批药品中的139件卸下并藏匿。然后继续办理托运手续将剩余药品依约发运至杭州。3天后,宋德明采取同样手段扣下药品8件。被告人宋德明两次共骗取药品147件,价值人民币20余万元。被告人宋德明将所扣药品变卖后携赃款逃匿并将赃款全部挥霍。
沈阳铁路运输法院认为,被告人宋德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后逃匿,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康恩贝公司长期委托宋德明代办托运药品,此次委托由康恩贝公司工作人员与宋德明达成口头协议,并就合同内容作出了具体约定,且宋已切实部分履行,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被告人宋德明的辩护人关于宋德明与被害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宋德明不是合同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第4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宋德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德明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
三、裁判理由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罪名。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刑法第266条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于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不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准确界定刑法第224条中“合同”的范围,是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一个先决问题,对于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诈骗两者界限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的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在本案中,首先,从事包装服务业务的被告人宋德明与被害单位康恩贝公司口头协议的事项为有偿代办托运,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的要求。其次,本案所涉口头合同具有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具备了特定标的、履行方式、劳务费等合同基本要件,且合同已经部分实际履行,结合此前双方已有的代办托运合作关系,足以证明该口头合同的真实存在。所以,将本案件口头合同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正确的。
(执笔: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陈佳茵 审编:叶晓颖)
选自《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
编者后记: 定合同诈骗罪还是一般诈骗罪,不能拘泥于形式,关键要看实质上有没有合同意思,是否按此在履行。否则有合同一样可以定一般诈骗。反之,没有签订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也可定合同诈骗。
【案例一】虽签订合同,但只是以此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定诈骗罪
基本案情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一个“辽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号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给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将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宜章介绍给王贺军。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张发两次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杨宜章等人见面,因此,杨宜章等人对王贺军深信不疑。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 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九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宣判后,王贺军以只在第一次骗了杨宜章30万元,后来拿的杨宜章的钱以及王惠明的20万元、王小岱的11万元是借,不是骗,并还了王小岱5万元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和能揽到工程项目的事实,以许诺给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巨大,原审将王贺军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不当。王贺军上诉提出其行为是借不是骗的上诉理由,经查,王贺军的多次供述及杨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陈述均证明,王贺军一开始即虚构身份,以许诺介绍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承包合同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向各被害人诈取钱财,并予以挥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另外,王小岱陈述王贺军没有还给他钱,王贺军也不能提供还钱的证据,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王贺军诈骗了杨宜章人民币72万元,但杨宜章陈述其被王贺军骗了70万元,故本院只认定王贺军诈骗杨宜章7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王贺军的上诉,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上诉人王贺军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七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二、主要问题
以许诺让他人承揽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王贺军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贺军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虚假的工程承揽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在合同签订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王贺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一)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从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但是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出发,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立法设立该罪以专惩此类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同为诈骗类侵财犯罪,两罪在构成要件上的共性特征以及具有的法条竞合关系使得如何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这也是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分歧意见的原因。我们认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其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签订是指自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同时,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全案事实,本案中被告人王贺军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执笔: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黄 燕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王志辉)
选自《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
【案例二】虽没有签订合同,但其骗取钱财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定合同诈骗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德明,男,34岁,初中文化。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1年9月30日被逮捕。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被告人宋德明犯合同诈骗罪,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宋德明对基本指控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宋德明与被害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宋德明不是合同当事人;被告人宋德明非法占有了哪些药品不清且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不能证明康恩贝公司丢失药品的数量和种类;认定数额特别巨大不当,应宣告被告人宋德明无罪。
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11月30日,从事包装服务业务的被告人宋德明接受浙江康恩贝集团医药销售公司(以下称康恩贝公司)工作人员的委托,为该公司在沈阳火车站发运药品。当日,被告人宋德明与该公司就代办运输、劳务费用、履行方式等具体内容达成口头协议。次日,被告人宋德明在康恩贝公司人员的陪同下,将首批应发运的药品从康恩贝公司药品仓库拉到沈阳火车站货场,装入集装箱并加锁。待康恩贝公司人员走后,宋将钥匙交给李某(搬运工)并指使李某将该批药品中的139件卸下并藏匿。然后继续办理托运手续将剩余药品依约发运至杭州。3天后,宋德明采取同样手段扣下药品8件。被告人宋德明两次共骗取药品147件,价值人民币20余万元。被告人宋德明将所扣药品变卖后携赃款逃匿并将赃款全部挥霍。
沈阳铁路运输法院认为,被告人宋德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后逃匿,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康恩贝公司长期委托宋德明代办托运药品,此次委托由康恩贝公司工作人员与宋德明达成口头协议,并就合同内容作出了具体约定,且宋已切实部分履行,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被告人宋德明的辩护人关于宋德明与被害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宋德明不是合同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第4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宋德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德明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
三、裁判理由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罪名。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刑法第266条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于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不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准确界定刑法第224条中“合同”的范围,是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一个先决问题,对于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诈骗两者界限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的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在本案中,首先,从事包装服务业务的被告人宋德明与被害单位康恩贝公司口头协议的事项为有偿代办托运,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的要求。其次,本案所涉口头合同具有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具备了特定标的、履行方式、劳务费等合同基本要件,且合同已经部分实际履行,结合此前双方已有的代办托运合作关系,足以证明该口头合同的真实存在。所以,将本案件口头合同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正确的。
(执笔: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陈佳茵 审编:叶晓颖)
选自《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
编者后记: 定合同诈骗罪还是一般诈骗罪,不能拘泥于形式,关键要看实质上有没有合同意思,是否按此在履行。否则有合同一样可以定一般诈骗。反之,没有签订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也可定合同诈骗。

免责声明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交流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更不作为营利使用。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作删除处理。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著作权等权利问题,请相关权利人根据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在两周内速来电、来函与智豪团队联系,本网承诺会及时删除处理。来电请拨打02363891336、13310240199。
- 相关阅读:
- · 被告人王某某在狱中冒充火车司机骗取钱财,犯诈骗罪合并前罪数罪并罚
- · 假扮寺庙主持骗人捐钱建寺庙、建佛像 被判诈骗罪获刑
- · 自动投案是否包括委托律师联系公安机关投案
- · 袁某采用裁剪、粘贴的方法,私造民事判决书欺骗当事人 被判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 · 冒充看守所公职人员、截取在押人员信件、伪造家书诈骗家属,被判诈骗罪获刑

我们的团队
更多>>
首席律师动态

亲办案例
查看更多罪名亲办案例
zhihaolawyer

微信号:zhihaolawyer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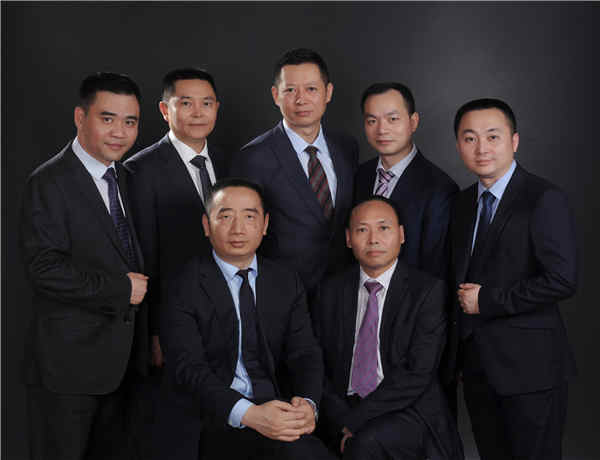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