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反思
导语:从另一角度来看,相关条文的出台在扩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却极大稀释了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人因其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负面评价,不利于未成年人知错就改,迷途知返。
有时,天真与罪恶只是一线之隔。
轰动一时的李某某强奸案,固然是该家庭教子无方致使少年人无序成长所引发的,但亦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剖析和反思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新视角。透过层层谜团,现有法律的一些框架性规定居于首施两端的尴尬状况时有显现。比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隐私保护,便与被害人保护及公众知情权存在着现实而紧迫的冲突。而加之这种冲突又暗合于涉案人的显赫家世与媒体炒作,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难度更是陡然增加了。
正是出于对这一年龄期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的考量,各法域无不主张对未成年人违法及轻微犯罪尽可能网开一面,以期其改过自新,这也是少年司法创设与延续的理念基石。
然而,上述理念尚不足以使得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掉以轻心或盲目乐观。因犯罪黑数使然,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过是实有犯罪之冰山一角,其确切数量及严重程度常常不为人所知。观之有关部门所公布的数据,几无悬念般地透露出未成年人犯罪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结论。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特别是证据规则的进一步从严把握,兼之法定从轻及酌定从轻的规定,许多未成年犯罪人被“过滤”出刑事司法体系。因而,对这些数据可能需要审慎的分析,数字本身并不一定如实反映出了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犯罪总量、趋势及特征,或只能大体说明业经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关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形。
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性不单单体现于绝对数量的增减,还体现在社会危害性、累犯率、犯罪后果等多重因素上。近年来,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与团伙化犯罪趋向明显,组织日渐团伙化、规模化及职能化,特别是未成年人“领衔”或主要参与其中的案例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之下,人为地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阻挡于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固然有避免标签化的合理考量。然而,看似“形势一片大好”,却可能很大程度上掩饰了现实中存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实况。18周岁前的低总量,却往往可能会在18周岁以后的统计中出现报复性急剧增长。当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数量、增减态势及表现形式因缺失循证评估,但这又直接关系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实现的力道。
一段时间以来,少年司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有意或无意将原本为非刑事化的少年司法完全或大体等同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并将两者的价值取向与体系程序混为一谈。而究其差异性,少年司法主要还应是对未成年不法行为人以及遭遇不法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所采取的紧急与积极干预,使得这些少年及时返回正常成长轨迹。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亲权”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儿童利益最佳”原则便生逢其时,与未成年人保护相生相荣。对这类未成年人特别是涉嫌不法与轻微犯罪的少年,考虑其心智未臻成熟,而采取诸如教育、感化等举措以达水到渠成之效。相应地,出于除罪化、除机构化及除污名化的考量,围绕着敦促不法少年改过自新和顺利重返社会的现实目标,一些程序性设计便体现出较为浓郁的儿童福利色彩,这显然是有别于以惩罚为基本导向的刑事司法的。
随着少年司法的发展,其在发挥矫正未成年人正面效果的同时,亦逐步显示出矫正效果不彰、被害人权益受损以及防卫社区忧虑等突出问题。正是基于此的现实考虑,少年司法在与刑事司法相互分离过程中,亦出现了水乳交融的趋势:少年司法及刑事司法现均愈发强调对未成年人归责性的追究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承担;而更早时间,刑事司法亦以多种形式重新取得了对犯有严重暴力犯罪少年以及屡次受少年司法矫正却效果不彰少年的管辖权,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少年法院成立后数年间便实现了的。
对于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实有必要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人格,反思现有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衡量其得失。未成年犯罪人除了具备一般人格涵义外,尚持有独特人格。其固然具有青涩及冲动之天性,亦不缺乏灰暗及自私放任的一面。对于前者,相信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多;但对于后者,可能支持的人亦不会太少。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出台时间并不长,1979年刑法制定时提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常被视为该政策之雏形。1991年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这一政策予以确认,并在1999年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明确。在此期间,两高两部相关司法解释及法规也多次重申了这一政策。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这自然可视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又一里程碑。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较难以视为少年司法的重大突破,而后者内核往往被视为非刑事化的。从另一角度来看,相关条文的出台在扩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却极大稀释了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人因其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负面评价,不利于未成年人知错就改,迷途知返。
当前亟需借鉴欧美有益经验,以归责性或可责性为导向,适时调整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汉语“归责”一词,语出《后汉书》,“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原意为将责任归咎于某人。而依《布莱克法律词典》,“culpability”通常系指“可责难性”以及“应受责备的质量”。汉语与英语语境下的“归责性”殊途同归,均大体指向对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拷问与追究。因归责性所系,相较于少年司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应当提供防卫社区、追究犯罪人对被害人及社区应承担的责任、培养犯罪人重返社区的能力。正是由于对“归责性”认知不明,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人犯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有时不免沦为一纸空文。从这几年的实证研究来看,许多未成年人便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赋予的特殊保护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以至司法,我们很多时候如走钢丝绳无异,总是希望在敦促未成年人改过自新与保护被害人及社区利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然而,若缺乏必要而充实的归责性导向,对未成年人的任何感化与教育都将无从落实。
归责性并不必然导致重刑化,近年来恢复性司法在各法域风头正盛便是例证。以归责性为依托,未成年加害人、被害人与社区及有关政府部门等各方在有关司法机关参与、调停并认证的情况下,以加害人认错为契机,责令其以各种不同方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来尽可能恢复遭其破坏的社会关系。
对未成年犯罪人归责性回归的强调,无关温柔杀戮,却有关即刻救赎。
导语:从另一角度来看,相关条文的出台在扩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却极大稀释了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人因其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负面评价,不利于未成年人知错就改,迷途知返。
有时,天真与罪恶只是一线之隔。
轰动一时的李某某强奸案,固然是该家庭教子无方致使少年人无序成长所引发的,但亦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剖析和反思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新视角。透过层层谜团,现有法律的一些框架性规定居于首施两端的尴尬状况时有显现。比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隐私保护,便与被害人保护及公众知情权存在着现实而紧迫的冲突。而加之这种冲突又暗合于涉案人的显赫家世与媒体炒作,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难度更是陡然增加了。
正是出于对这一年龄期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的考量,各法域无不主张对未成年人违法及轻微犯罪尽可能网开一面,以期其改过自新,这也是少年司法创设与延续的理念基石。
然而,上述理念尚不足以使得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掉以轻心或盲目乐观。因犯罪黑数使然,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过是实有犯罪之冰山一角,其确切数量及严重程度常常不为人所知。观之有关部门所公布的数据,几无悬念般地透露出未成年人犯罪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结论。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特别是证据规则的进一步从严把握,兼之法定从轻及酌定从轻的规定,许多未成年犯罪人被“过滤”出刑事司法体系。因而,对这些数据可能需要审慎的分析,数字本身并不一定如实反映出了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犯罪总量、趋势及特征,或只能大体说明业经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关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形。
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性不单单体现于绝对数量的增减,还体现在社会危害性、累犯率、犯罪后果等多重因素上。近年来,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与团伙化犯罪趋向明显,组织日渐团伙化、规模化及职能化,特别是未成年人“领衔”或主要参与其中的案例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之下,人为地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阻挡于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固然有避免标签化的合理考量。然而,看似“形势一片大好”,却可能很大程度上掩饰了现实中存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实况。18周岁前的低总量,却往往可能会在18周岁以后的统计中出现报复性急剧增长。当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数量、增减态势及表现形式因缺失循证评估,但这又直接关系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实现的力道。
一段时间以来,少年司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有意或无意将原本为非刑事化的少年司法完全或大体等同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并将两者的价值取向与体系程序混为一谈。而究其差异性,少年司法主要还应是对未成年不法行为人以及遭遇不法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所采取的紧急与积极干预,使得这些少年及时返回正常成长轨迹。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亲权”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儿童利益最佳”原则便生逢其时,与未成年人保护相生相荣。对这类未成年人特别是涉嫌不法与轻微犯罪的少年,考虑其心智未臻成熟,而采取诸如教育、感化等举措以达水到渠成之效。相应地,出于除罪化、除机构化及除污名化的考量,围绕着敦促不法少年改过自新和顺利重返社会的现实目标,一些程序性设计便体现出较为浓郁的儿童福利色彩,这显然是有别于以惩罚为基本导向的刑事司法的。
随着少年司法的发展,其在发挥矫正未成年人正面效果的同时,亦逐步显示出矫正效果不彰、被害人权益受损以及防卫社区忧虑等突出问题。正是基于此的现实考虑,少年司法在与刑事司法相互分离过程中,亦出现了水乳交融的趋势:少年司法及刑事司法现均愈发强调对未成年人归责性的追究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承担;而更早时间,刑事司法亦以多种形式重新取得了对犯有严重暴力犯罪少年以及屡次受少年司法矫正却效果不彰少年的管辖权,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少年法院成立后数年间便实现了的。
对于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实有必要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人格,反思现有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衡量其得失。未成年犯罪人除了具备一般人格涵义外,尚持有独特人格。其固然具有青涩及冲动之天性,亦不缺乏灰暗及自私放任的一面。对于前者,相信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多;但对于后者,可能支持的人亦不会太少。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出台时间并不长,1979年刑法制定时提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常被视为该政策之雏形。1991年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这一政策予以确认,并在1999年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明确。在此期间,两高两部相关司法解释及法规也多次重申了这一政策。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这自然可视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又一里程碑。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较难以视为少年司法的重大突破,而后者内核往往被视为非刑事化的。从另一角度来看,相关条文的出台在扩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却极大稀释了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人因其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负面评价,不利于未成年人知错就改,迷途知返。
当前亟需借鉴欧美有益经验,以归责性或可责性为导向,适时调整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汉语“归责”一词,语出《后汉书》,“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原意为将责任归咎于某人。而依《布莱克法律词典》,“culpability”通常系指“可责难性”以及“应受责备的质量”。汉语与英语语境下的“归责性”殊途同归,均大体指向对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拷问与追究。因归责性所系,相较于少年司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应当提供防卫社区、追究犯罪人对被害人及社区应承担的责任、培养犯罪人重返社区的能力。正是由于对“归责性”认知不明,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人犯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有时不免沦为一纸空文。从这几年的实证研究来看,许多未成年人便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赋予的特殊保护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以至司法,我们很多时候如走钢丝绳无异,总是希望在敦促未成年人改过自新与保护被害人及社区利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然而,若缺乏必要而充实的归责性导向,对未成年人的任何感化与教育都将无从落实。
归责性并不必然导致重刑化,近年来恢复性司法在各法域风头正盛便是例证。以归责性为依托,未成年加害人、被害人与社区及有关政府部门等各方在有关司法机关参与、调停并认证的情况下,以加害人认错为契机,责令其以各种不同方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来尽可能恢复遭其破坏的社会关系。
对未成年犯罪人归责性回归的强调,无关温柔杀戮,却有关即刻救赎。

免责声明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交流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更不作为营利使用。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作删除处理。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著作权等权利问题,请相关权利人根据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在两周内速来电、来函与智豪团队联系,本网承诺会及时删除处理。来电请拨打02363891336、13310240199。
- 相关阅读:

我们的团队
更多>>
首席律师动态

亲办案例
查看更多罪名亲办案例
zhihaolawyer

微信号:zhihaolawyer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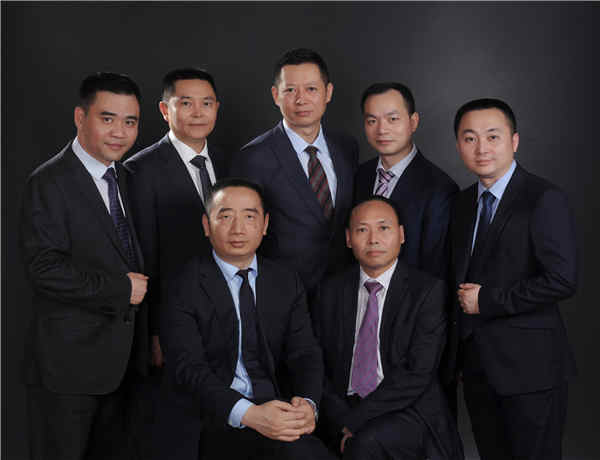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