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不能适用刑法“但书”出罪
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情节犯,立法者认为,满足“醉酒”这个情节的危险驾驶行为就成立犯罪,而不能再去考虑是否存在“情节显著轻微”。
醉酒驾驶带来的危险的高低,是犯罪基准之上的危害程度的问题,影响的是量刑,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醉酒驾驶是否一律构成犯罪,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律论”和“不必论”都有人主张,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再次探讨醉酒驾驶是否一律构成犯罪这一论题。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第133条之一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依据这一规定,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行为以情节恶劣为其构罪要求,而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没有情节方面的要求。对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和适用似乎并不存在问题,但对于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和适用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混乱。有人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只要醉酒驾驶即构成犯罪;有人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仅有醉酒驾驶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犯罪,还需存在侵害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只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予以出罪。另有观点认为,“醉驾”可以出罪,但无需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3年12月18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细化了诸如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及从重处罚的8种情节等内容。然而,《意见》并未消除理论上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的不一。
刑法学属于规范科学,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成为刑法学的重点。没有刑法规范的解释,就没有刑法学。危险驾驶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危险驾驶罪不可能停留在对中性的驾驶行为的评价上,因为对中性的驾驶行为的评价毫无刑法意义。危险驾驶罪的刑法意义在于对驾驶行为的危险性进行实质评价。在罪名结构上,“驾驶”是中性的,“危险”一词是“危险驾驶”的核心价值要素,“危险”从词语构成上修饰“驾驶”,对“驾驶”进行负面评价。“罪”是对“危险驾驶”的量的要求。评判危险驾驶罪的成立应该是危险状态的出现而不是驾驶行为的实施。所以,从罪名结构上分析,危险驾驶罪应该是危险犯而不是行为犯。在刑法学界客观主义刑法思潮日渐高涨的今天,肯定单纯的行为犯不利于保护人权。具体而言,如果单纯考察行为人的醉酒驾驶行为,而不考察行为的危险性,必然会导致犯罪圈的扩大,把没有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也认定为犯罪,而这也有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以,醉酒驾驶行为是否产生了法益侵害的危险,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实施了产生法益侵害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才构成危险驾驶罪。
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指行为已经引起刑法保护客体的危险,此危险是一种需要司法上具体判断之危险,且可以在经验上被感知,其在法律条文中常以“足以……危险”字句出现。例如,刑法第117条破坏交通设施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因为它明文规定了具体危险——“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抽象危险犯,是指伴随立法上类型化的行为的出现,危险状态即已出现。此危险是一种立法上的拟制,不需要司法的具体判断,只要实施了类型化的行为即认定有危险。抽象危险犯有两种:明文规定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和没有明文规定危险的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第118条破坏电力设备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属于明文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它规定了抽象的危险——“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第369条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属于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危险的抽象危险犯,法条只规定了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并没有规定抽象的危险即构成犯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没有明文规定危险的第三种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有其共同点,即都是类型化的行为,都会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只不过具体危险犯的危险可被感知,需要司法上作出具体判断;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类型化行为的结果,只要实施了类型化的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就已经产生。可见,较之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成立门槛明显较低。而刑法之所以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方式,本质上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
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之规范构造
危险犯与情节犯对犯罪的分类标准不同,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但这并不意味着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不能同时属于情节犯,事实上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在刑法理论中,情节犯是指需要一定情节才能构成的犯罪类型。但情节犯不仅仅指法条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字样的犯罪,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情节犯——总则式情节犯,这是一种非明示的情节犯,指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但可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规定的情节犯。
无论“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还是“情节显著轻微”,其明文表述的“情节”都是概括性的,没有指明具体的情节内容。而情节犯中的“情节”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既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犯罪手段、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情景、犯罪结果、犯罪对象、犯罪次数、犯罪动机、行为人主观恶性及状态等。刑法对这些具体情节作概括性的规定,意味着不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强调,只要有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达到了严重或恶劣的程度,其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情节分为概括情节和具体情节,而判断情节是否严重或恶劣,要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确定。
笔者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既不属于分则明文规定 “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情节犯,也不属于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排除式情节犯,而是由分则规定的具体情节犯,其情节表现为“醉酒”。立法者认为,作为具体定罪情节,满足“醉酒”这个情节的危险驾驶成立犯罪,而不能对已经醉酒驾驶的情况,再去考虑是否存在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如果把“醉酒驾驶”中的“醉酒”理解为行为,则使“醉酒”失去独立的具体情节意义,认为“醉酒驾驶”不同于“追逐竞驶”。“追逐竞驶”部分明文规定了“情节恶劣”,表明是情节犯,而“醉酒驾驶”部分没有出现有关情节的表述,因而只好到总则中找情节,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也许有人认为,在完全空旷的地方醉酒驾驶,可以是情节显著轻微而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即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如果是在无人无车的道路上醉酒行使,根本不可能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一个不可能给他人带来危险的行为根本不是犯罪,因而也就涉及不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适用问题。
还有人提出,虽然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酒法定界限值,但精神状态健全,尚有正常的驾驶能力,注意力并未降低,而且以极低的速度于清晨驾车返回家中,对此若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必然与公民的感情以及罪责相适应原则相冲突。继而提出,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则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以下误区:第一,所谓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酒法定界限值,但精神状态健全,尚有正常的驾驶能力,注意力并未降低,是以个人酒量不同来强调区别定罪的必要,而这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虽然自己觉得很清醒,根本没醉,但血液酒精浓度却已经达到醉酒的标准。而且法律是从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出发,不可能因人而异照顾那些酒量超群的人。虽然从社会个体角度看,每个人在生理上对酒精的反应度不同,但是从法律角度看,“醉酒驾驶”是一种面对社会普通人进行衡量的客观标准,与具体行为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不存在必然联系。第二,清晨以极低的速度醉酒后谨慎驾驶,一般不会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那么这种驾驶行为是否还能被称之为刑法意义的醉酒驾驶,恐怕还需研究,因为没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便不可能进入刑法视域。关于此,前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第三,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根据是行为,只要符合醉酒程度的驾驶,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醉酒驾驶带来的危险的高低,是犯罪基准之上的危害程度的问题,影响的是量刑,即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虑,而不能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总之,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抽象危险犯而言,这种抽象危险的判定是基于对行为的认定——这种现实存在的危险本身是一种达到了犯罪程度的情节,继而排除了情节显著轻微的可能,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在危险的判定中没有适用空间。担心“醉酒驾驶”一律构成犯罪会使打击面过大,已经不是司法问题,而是立法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过程中被充分考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如果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出现的时段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危险,则该行为不会构成犯罪。另外,如果存在排除犯罪性事由,即便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醉酒驾驶行为也不成立犯罪。
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情节犯,立法者认为,满足“醉酒”这个情节的危险驾驶行为就成立犯罪,而不能再去考虑是否存在“情节显著轻微”。
醉酒驾驶带来的危险的高低,是犯罪基准之上的危害程度的问题,影响的是量刑,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醉酒驾驶是否一律构成犯罪,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律论”和“不必论”都有人主张,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再次探讨醉酒驾驶是否一律构成犯罪这一论题。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第133条之一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依据这一规定,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行为以情节恶劣为其构罪要求,而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没有情节方面的要求。对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和适用似乎并不存在问题,但对于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和适用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混乱。有人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只要醉酒驾驶即构成犯罪;有人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仅有醉酒驾驶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犯罪,还需存在侵害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只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予以出罪。另有观点认为,“醉驾”可以出罪,但无需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3年12月18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细化了诸如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及从重处罚的8种情节等内容。然而,《意见》并未消除理论上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的不一。
刑法学属于规范科学,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成为刑法学的重点。没有刑法规范的解释,就没有刑法学。危险驾驶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危险驾驶罪不可能停留在对中性的驾驶行为的评价上,因为对中性的驾驶行为的评价毫无刑法意义。危险驾驶罪的刑法意义在于对驾驶行为的危险性进行实质评价。在罪名结构上,“驾驶”是中性的,“危险”一词是“危险驾驶”的核心价值要素,“危险”从词语构成上修饰“驾驶”,对“驾驶”进行负面评价。“罪”是对“危险驾驶”的量的要求。评判危险驾驶罪的成立应该是危险状态的出现而不是驾驶行为的实施。所以,从罪名结构上分析,危险驾驶罪应该是危险犯而不是行为犯。在刑法学界客观主义刑法思潮日渐高涨的今天,肯定单纯的行为犯不利于保护人权。具体而言,如果单纯考察行为人的醉酒驾驶行为,而不考察行为的危险性,必然会导致犯罪圈的扩大,把没有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也认定为犯罪,而这也有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以,醉酒驾驶行为是否产生了法益侵害的危险,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实施了产生法益侵害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才构成危险驾驶罪。
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指行为已经引起刑法保护客体的危险,此危险是一种需要司法上具体判断之危险,且可以在经验上被感知,其在法律条文中常以“足以……危险”字句出现。例如,刑法第117条破坏交通设施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因为它明文规定了具体危险——“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抽象危险犯,是指伴随立法上类型化的行为的出现,危险状态即已出现。此危险是一种立法上的拟制,不需要司法的具体判断,只要实施了类型化的行为即认定有危险。抽象危险犯有两种:明文规定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和没有明文规定危险的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第118条破坏电力设备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属于明文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它规定了抽象的危险——“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第369条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属于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危险的抽象危险犯,法条只规定了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并没有规定抽象的危险即构成犯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没有明文规定危险的第三种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有其共同点,即都是类型化的行为,都会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只不过具体危险犯的危险可被感知,需要司法上作出具体判断;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类型化行为的结果,只要实施了类型化的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就已经产生。可见,较之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成立门槛明显较低。而刑法之所以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方式,本质上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
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之规范构造
危险犯与情节犯对犯罪的分类标准不同,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但这并不意味着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不能同时属于情节犯,事实上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在刑法理论中,情节犯是指需要一定情节才能构成的犯罪类型。但情节犯不仅仅指法条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字样的犯罪,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情节犯——总则式情节犯,这是一种非明示的情节犯,指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但可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规定的情节犯。
无论“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还是“情节显著轻微”,其明文表述的“情节”都是概括性的,没有指明具体的情节内容。而情节犯中的“情节”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既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犯罪手段、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情景、犯罪结果、犯罪对象、犯罪次数、犯罪动机、行为人主观恶性及状态等。刑法对这些具体情节作概括性的规定,意味着不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强调,只要有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达到了严重或恶劣的程度,其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情节分为概括情节和具体情节,而判断情节是否严重或恶劣,要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确定。
笔者认为,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既不属于分则明文规定 “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情节犯,也不属于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排除式情节犯,而是由分则规定的具体情节犯,其情节表现为“醉酒”。立法者认为,作为具体定罪情节,满足“醉酒”这个情节的危险驾驶成立犯罪,而不能对已经醉酒驾驶的情况,再去考虑是否存在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如果把“醉酒驾驶”中的“醉酒”理解为行为,则使“醉酒”失去独立的具体情节意义,认为“醉酒驾驶”不同于“追逐竞驶”。“追逐竞驶”部分明文规定了“情节恶劣”,表明是情节犯,而“醉酒驾驶”部分没有出现有关情节的表述,因而只好到总则中找情节,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也许有人认为,在完全空旷的地方醉酒驾驶,可以是情节显著轻微而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即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如果是在无人无车的道路上醉酒行使,根本不可能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一个不可能给他人带来危险的行为根本不是犯罪,因而也就涉及不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适用问题。
还有人提出,虽然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酒法定界限值,但精神状态健全,尚有正常的驾驶能力,注意力并未降低,而且以极低的速度于清晨驾车返回家中,对此若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必然与公民的感情以及罪责相适应原则相冲突。继而提出,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则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以下误区:第一,所谓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酒法定界限值,但精神状态健全,尚有正常的驾驶能力,注意力并未降低,是以个人酒量不同来强调区别定罪的必要,而这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虽然自己觉得很清醒,根本没醉,但血液酒精浓度却已经达到醉酒的标准。而且法律是从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出发,不可能因人而异照顾那些酒量超群的人。虽然从社会个体角度看,每个人在生理上对酒精的反应度不同,但是从法律角度看,“醉酒驾驶”是一种面对社会普通人进行衡量的客观标准,与具体行为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不存在必然联系。第二,清晨以极低的速度醉酒后谨慎驾驶,一般不会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那么这种驾驶行为是否还能被称之为刑法意义的醉酒驾驶,恐怕还需研究,因为没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便不可能进入刑法视域。关于此,前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第三,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根据是行为,只要符合醉酒程度的驾驶,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醉酒驾驶带来的危险的高低,是犯罪基准之上的危害程度的问题,影响的是量刑,即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虑,而不能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总之,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抽象危险犯而言,这种抽象危险的判定是基于对行为的认定——这种现实存在的危险本身是一种达到了犯罪程度的情节,继而排除了情节显著轻微的可能,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在危险的判定中没有适用空间。担心“醉酒驾驶”一律构成犯罪会使打击面过大,已经不是司法问题,而是立法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过程中被充分考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如果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出现的时段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危险,则该行为不会构成犯罪。另外,如果存在排除犯罪性事由,即便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醉酒驾驶行为也不成立犯罪。
上一篇:简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关系
下一篇:转化型抢劫罪转化条件的认定

免责声明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交流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更不作为营利使用。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作删除处理。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著作权等权利问题,请相关权利人根据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在两周内速来电、来函与智豪团队联系,本网承诺会及时删除处理。来电请拨打02363891336、13310240199。
- 相关阅读:

我们的团队
更多>>
首席律师动态

亲办案例
查看更多罪名亲办案例
zhihaolawyer

微信号:zhihaolawyer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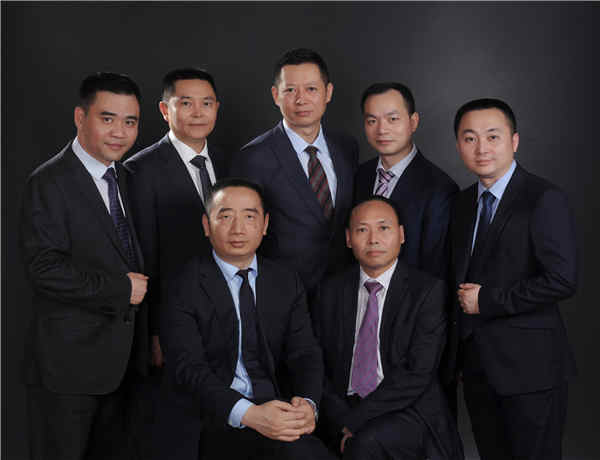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