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金钟西路17号.
法定代表人邹正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俊,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艺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平,董事长。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佟洁,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简称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因与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简称新画面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原审法院)于2011年5月24日作出的(2010)西民初字第2606号民事判决(简称原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1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法定代表人邹正明、委托代理人李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佟洁、林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原审诉称:由新画面公司作为出品人、张伟平为制片人、张艺谋为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拍摄时邀请了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八位地戏演员前往丽江,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并将八位地戏演员表演的上述剧目剪辑到了电影《千里走单骑》中。但该影片中却将其称之为“云南面具戏”,且上述三被告没有在任何场合为影片中“云南面具戏”的真实身份正名,以致观众以为影片中的面具戏的起源地、传承地就在云南。该影片中将具有特殊地域性、表现唯一性的“安顺地戏”误导成“云南面具戏”,歪曲了“安顺地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并在事实上误导了中外观众,造成前往云南寻找影片中的面具戏的严重后果。据此,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请求法院判令: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分别在《法制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新画面公司在以任何方式再使用影片《千里走单骑》时,应当注明“片中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是‘安顺地戏’”。
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原审辩称:影片《千里走单骑》的出品人是新画面公司,出品人是电影作品的所有人,故要求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对张艺谋、张伟平的诉讼请求。《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2006年5月,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无权追溯主张署名权。况且,《千里走单骑》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而非一个专门介绍傩戏、面具戏或地戏的专题片或纪录片,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不能要求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被告承担将艺术虚构与真实存在相互对接的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根据史料记载,“安顺地戏”是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历史上“屯田戍边”将士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是流行于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的一种地方戏剧。2006年6月,国务院将“安顺地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4年11月1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为新画面公司、香港精英集团(2004)企业有限公司颁发《中外合作摄制电影许可证》,许可证载明,“影片名称《千里走单骑》,中方摄制单位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外方摄制单位香港精英集团(2004)企业有限公司”。
2005年7月1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出品人为新画面公司。该影片片头字幕显示的相关制作人员包括编剧、导演张艺谋,制片张伟平等。
影片《千里走单骑》讲述的是两对父子的故事,反映的外景环境为中国云南省的丽江。影片放映至6分16秒时,画面出现了戏剧表演《千里走单骑》,此时出现画外音:“这是中国云南面具戏”。影片中戏剧表演者有新画面公司从贵州省安顺市詹家屯“三国戏曲演出队”所聘请的演员。在该影片片尾字幕出现的演职员名单中标示有“戏曲演出:贵州省安顺市詹家屯三国戏队詹学彦等八人”字样。
以上事实,有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光盘、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涉案电影海报、影院入场券以及庭审笔录等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史料记载,“安顺地戏”是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历史上“屯田戍边”将士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在世代相传、继承、修改和丰富下形成了现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安顺地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保存,任何非法侵占、破坏、歪曲和毁损等侵害和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继承和弘扬的行为都应当予以禁止和摒弃;任何使用者包括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等都应当尊重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审理本案,已经看到“安顺地戏”不断得到包括原告在内的国家各级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的重视,保护、保存意识和措施也不断增强和完善。然而,作为负有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以自己名义提起与他人著作权侵权诉讼时,首先应当严格依照现有《著作权法》和相关法规的规定行事。
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关注人性、亲情的故事影片,贯穿全剧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父子情。就整体影片来说,联系两对父子的“傩戏”仅仅是故事的一个引子,并非该影片的重心。被告将真实存在的“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素材用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作品中,但被告在具体使用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使之表现形式符合电影创作的需要更加丰富与感人,并为了烘托整个影片反映的大环境与背景,将其称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 “云南面具戏”。此种演绎拍摄手法符合电影创作的规律,区别于不得虚构的新闻纪录片。
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断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但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故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法院也愿意提醒作为电影事业从业者的被告,今后更应当增强对我国《著作权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习运用,谨慎从业,尽可能预防和避免民事纠纷的发生。
综上所述,“安顺地戏”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应当依法予以高度的尊重与保护,这并无疑义。但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安顺地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未在任何场合对此予以澄清,其行为构成了对“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的侵犯,违反了《著作权法》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1、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始终主张的是被控侵权行为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从未提及“安顺地戏”的著作权人是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也从未提及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署名权被侵犯,但在原审判决书的“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诉称”部分却被写成了“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2、原审判决将案件的重点放在影片是否可以利用“安顺地戏”进行虚构演绎,歪曲了上诉人的诉讼本意。上诉人无意也无权禁止被上诉人使用‘安顺地戏’进行虚构创作,而仅是要求被上诉人在使用“安顺地戏”后应当标注其名称,也就是说,上诉人不是要求将影片中的画外音“这是中国云南省的面具戏”改成“这是中国贵州省的安顺地戏”,而是要求在被上诉人保留影片原有画外音的情况下,在片尾或其他场合标明影片中的云南面具戏的艺术元素来自“安顺地戏”。但原审判决中认定,“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这是对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误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3、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段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不仅主观上存在过错,其行为客观上亦已造成误导的实际后果,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亦已提交证据证明误导后果的存在。据此,原审判决中的上述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4、《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在具体使用“安顺地戏”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但却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上述使用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仍坚持原审诉讼中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安顺地戏”并不能够依据《著作权法》享有署名权,涉案电影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并未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同时,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与‘安顺地戏’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其并无资格提起本案诉讼,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因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原审判决在“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诉称”部分有“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这一表述。
原审起诉状中针对被控侵权行为的相应表述为“三被告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中使用了‘安顺地戏’,并把‘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却没有在任何场合进行说明,澄清事实,这种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
庭审中,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著作权法》署名权中的“名”应理解为既包括作者的名称,亦包括作品的名称,本案中则指向的是作品的名称。“安顺地戏”虽是一种剧种,但其亦属于作品,被上诉人在使用时应对该作品名称予以标注,但其并未标注,故其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
上述事实有原审判决、原审起诉状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焦点问题:
一、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可知,民事案件的适格原告应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因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故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只有在与“安顺地戏”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由查明事实可知,“安顺地戏”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由安顺地区的人民世代相传、继承、丰富而成。因这一文化遗产系安顺地区人民共同创作并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并不归属于某个特定民事主体,因此,当他人的使用行为对这一文化遗产造成损害时,难以由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主张权利。
本案中,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虽然并非“安顺地戏”的权利人,但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七条的规定,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在“安顺地戏”已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下,作为“安顺地戏”的管理及保护机关,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有资格代表安顺地区的人民就他人侵害“安顺地戏”的行为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据此,本院认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是否应为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指控的侵权行为系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地戏”错误地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不对其予以澄清的行为,因此,判断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是否应为这一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均有义务对涉案电影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由该规定可知,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享有,制片者有权就电影作品对外行使著作权并获得利益。编剧、导演等民事主体虽享有署名权,但其并非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就电影作品对外行使著作权并获益。虽然《著作权法》中对基于电影作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并无明确规定,但基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相对等的原则,权利人在行使民事权利的同时亦有义务承担基于该权利客体而产生的相应责任,故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作为著作权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亦当然应承担基于该电影作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据此,本案中,基于涉案电影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涉案电影的制片者,而非编剧、导演等其他民事主体承担。
因《著作权法》中对于作为著作权人的“制片者”在电影作品中的标注形式并无要求,实践中亦存在多种标注方式,故对制片者身份的认定应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予以考虑,而不能仅依据电影作品中的标注形式予以确定。同时应注意的是,《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制片者”并不等同于具体电影作品中标注的“制片”或“制片人”,前者系《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用语,是指对电影作品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后者系电影行业中的用语,二者并非当然是同一主体。
具体到本案,虽然张伟平在涉案电影中标注为“制片人”,但这一标注并不相当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制片者。在涉案电影中标注的出品单位及《电影公映许可证》中载明的出品人均为新画面公司的情况下,结合电影行业的惯例,本院合理认为涉案电影的制片者应为新画面公司,新画面公司对涉案电影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其系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主体。张艺谋仅系涉案电影的编剧、导演,其并非涉案电影的制片者,张伟平亦非涉案电影的制片者,故张艺谋、张伟平均非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主体,不应对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三、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涉案电影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方式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侵犯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安顺地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未在任何场合对此予以澄清,其行为构成了对“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的侵犯,违反了《著作权法》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
对此,本院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著作权法》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侧重于行政保护,《著作权法》则侧重于民事保护,二者具有不同的立法宗旨、保护方式及保护条件。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亦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安顺地戏”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实仅意味着其应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至于其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还要看其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的相应规定。
具体到本案,因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的是“安顺地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署名权,故本案的审理应以《著作权法》中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及署名权的相关规定为法律依据。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一特殊类型的作品,《著作权法》中尚无具体规定,只是在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尚未制定出相关的著作权保护办法。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立足于《著作权法》,故在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关著作权保护办法的情况下,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对其署名权的保护亦不例外。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知,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是“作者”,权利客体是具体的“作品”,权利内容是在作品上标注作者的名称。也就是说,署名权中的“名”指的是权利主体(即作者)的名称,而非权利客体(即作品)的名称,他人只有在使用作品而未署“作者”的名称时,其行为才可能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至于是否标注了“作品”的名称,则并非署名权调整的范围。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将署名权理解为对“作品”名称的标注,这一理解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在此基础上,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的规定,如果本案事实同时符合下述两要件,则可以认定涉案电影中的使用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首先,“安顺地戏”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中有关署名权的要求;其次,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属于受《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
对于“安顺地戏”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中有关署名权的要求,本院认为,依据上述规定,只有当“安顺地戏”或者是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即作者),或者是权利客体(即作品)的情况下,其才可能获得《著作权法》署名权的保护。因“安顺地戏”显然并非权利主体(即作者),故本案的判断关键在于其是否构成署名权的权利客体(即作品)。如“安顺地戏”构成作品,则应进一步对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的“安顺地戏”这一标注方式是否属于“作者”的署名予以判断。
对于“安顺地戏”是否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本院认为,依据《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只有对思想的具体表达才可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其仅是具有特定特征的戏剧剧目的总称,是对戏剧类别的划分,而非对于具体思想的表达,故“安顺地戏”并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任何人均不能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享有署名权。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安顺地戏”虽是一种剧种,但其亦属于作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其不构成作品,并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故对于“安顺地戏”这一标注方式是否属于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作者”的署名方式这一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本院对此将不予论及。
在此基础上,本院进一步对于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受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予以评述。本院认为,基于与“安顺地戏”相同的理由,涉案电影中对于“云南面具戏”这一名称的使用,亦仅属于对于特定剧种名称的使用,其既非对署名权权利主体(作者)的标注,亦非对权利客体(作品)的标注,故这一使用方式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同时,本院亦认为,涉案电影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使用的艺术元素进行相应虚构,具有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虽涉案电影中实施了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且未对此予以澄清,但鉴于“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其不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的规定,任何主体无法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享有署名权,且涉案电影中“云南面具戏”这一名称的使用亦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故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上述行为不可能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上述行为侵犯了“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应指出的是,因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明确主张构成作品且享有署名权的是“安顺地戏”,而非其中的“具体剧目”,故本院作出的上述认定仅针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而未涉及其中的“具体剧目”。对于“安顺地戏”中的具体剧目(如涉案电影中使用的《千里走单骑》等剧目),本院认为,因其属于对于思想的具体表达,故可以认定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事主体可以针对具体剧目主张署名权。
四、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中将原审起诉状中表述的“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理解为“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这一理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在原审起诉状中确有“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这一表述,依据上述表述进行字面理解,通常会理解为其主张享有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为“安顺地戏”,但因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而“安顺地戏”显非民事主体,其不可能成为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故上述字面理解显然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亦不符合常理。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考虑到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系作为“安顺地戏”权利人代表提起诉讼这一因素,将上述表述合理理解为“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其虽在表述上有失严谨,但尚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据此,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中认定“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这一认定系对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误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原审诉讼本意的理解来源于其起诉状中的具体文字表述,起诉状中对于被控侵权行为的表述主要为“三被告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中使用了‘安顺地戏’并把‘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却没有在任何场合进行说明,澄清事实,这种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本院认为,起诉状中上述文字表述可以合理理解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仅是要求“被上诉人保留影片原有画外音的情况下,在片尾或其他场合标明影片中的云南面具戏的艺术元素来自安顺地戏”这一含义仅从上述文字表述中无法当然得知,据此,原审法院基于其对原审起诉状的理解,对于“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是否违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予以认定,并未违反上诉人原审起诉状中所体现出的意思表示,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段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为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故原审法院应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在“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的情况下,其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从《著作权法》角度进行判断,被上诉人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行为其主观并无过错,客观上亦未对著作权本身造成损害后果。据此,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无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在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在具体使用“安顺地戏”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的情况下,却未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上述使用行为构成对其署名权的侵犯,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依据上述规定,只有他人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的系“已有作品”的情况下,才需要经过原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鉴于本院已认定“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不构成作品,并非《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故上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审判决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涉案电影中的使用行为构成侵权,其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著作权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七百五十元,均由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定代表人邹正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俊,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艺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平,董事长。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佟洁,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简称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因与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简称新画面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原审法院)于2011年5月24日作出的(2010)西民初字第2606号民事判决(简称原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1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法定代表人邹正明、委托代理人李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佟洁、林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原审诉称:由新画面公司作为出品人、张伟平为制片人、张艺谋为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拍摄时邀请了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八位地戏演员前往丽江,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并将八位地戏演员表演的上述剧目剪辑到了电影《千里走单骑》中。但该影片中却将其称之为“云南面具戏”,且上述三被告没有在任何场合为影片中“云南面具戏”的真实身份正名,以致观众以为影片中的面具戏的起源地、传承地就在云南。该影片中将具有特殊地域性、表现唯一性的“安顺地戏”误导成“云南面具戏”,歪曲了“安顺地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并在事实上误导了中外观众,造成前往云南寻找影片中的面具戏的严重后果。据此,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请求法院判令: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分别在《法制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新画面公司在以任何方式再使用影片《千里走单骑》时,应当注明“片中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是‘安顺地戏’”。
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原审辩称:影片《千里走单骑》的出品人是新画面公司,出品人是电影作品的所有人,故要求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对张艺谋、张伟平的诉讼请求。《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2006年5月,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无权追溯主张署名权。况且,《千里走单骑》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而非一个专门介绍傩戏、面具戏或地戏的专题片或纪录片,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不能要求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被告承担将艺术虚构与真实存在相互对接的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根据史料记载,“安顺地戏”是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历史上“屯田戍边”将士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是流行于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的一种地方戏剧。2006年6月,国务院将“安顺地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4年11月1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为新画面公司、香港精英集团(2004)企业有限公司颁发《中外合作摄制电影许可证》,许可证载明,“影片名称《千里走单骑》,中方摄制单位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外方摄制单位香港精英集团(2004)企业有限公司”。
2005年7月1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出品人为新画面公司。该影片片头字幕显示的相关制作人员包括编剧、导演张艺谋,制片张伟平等。
影片《千里走单骑》讲述的是两对父子的故事,反映的外景环境为中国云南省的丽江。影片放映至6分16秒时,画面出现了戏剧表演《千里走单骑》,此时出现画外音:“这是中国云南面具戏”。影片中戏剧表演者有新画面公司从贵州省安顺市詹家屯“三国戏曲演出队”所聘请的演员。在该影片片尾字幕出现的演职员名单中标示有“戏曲演出:贵州省安顺市詹家屯三国戏队詹学彦等八人”字样。
以上事实,有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光盘、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涉案电影海报、影院入场券以及庭审笔录等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史料记载,“安顺地戏”是我国贵州省安顺地区历史上“屯田戍边”将士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在世代相传、继承、修改和丰富下形成了现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安顺地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保存,任何非法侵占、破坏、歪曲和毁损等侵害和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继承和弘扬的行为都应当予以禁止和摒弃;任何使用者包括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等都应当尊重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审理本案,已经看到“安顺地戏”不断得到包括原告在内的国家各级有关机关和社会公众的重视,保护、保存意识和措施也不断增强和完善。然而,作为负有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以自己名义提起与他人著作权侵权诉讼时,首先应当严格依照现有《著作权法》和相关法规的规定行事。
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关注人性、亲情的故事影片,贯穿全剧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父子情。就整体影片来说,联系两对父子的“傩戏”仅仅是故事的一个引子,并非该影片的重心。被告将真实存在的“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素材用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作品中,但被告在具体使用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使之表现形式符合电影创作的需要更加丰富与感人,并为了烘托整个影片反映的大环境与背景,将其称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 “云南面具戏”。此种演绎拍摄手法符合电影创作的规律,区别于不得虚构的新闻纪录片。
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断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但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故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法院也愿意提醒作为电影事业从业者的被告,今后更应当增强对我国《著作权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习运用,谨慎从业,尽可能预防和避免民事纠纷的发生。
综上所述,“安顺地戏”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应当依法予以高度的尊重与保护,这并无疑义。但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诉讼请求。
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安顺地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未在任何场合对此予以澄清,其行为构成了对“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的侵犯,违反了《著作权法》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1、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始终主张的是被控侵权行为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从未提及“安顺地戏”的著作权人是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也从未提及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署名权被侵犯,但在原审判决书的“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诉称”部分却被写成了“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2、原审判决将案件的重点放在影片是否可以利用“安顺地戏”进行虚构演绎,歪曲了上诉人的诉讼本意。上诉人无意也无权禁止被上诉人使用‘安顺地戏’进行虚构创作,而仅是要求被上诉人在使用“安顺地戏”后应当标注其名称,也就是说,上诉人不是要求将影片中的画外音“这是中国云南省的面具戏”改成“这是中国贵州省的安顺地戏”,而是要求在被上诉人保留影片原有画外音的情况下,在片尾或其他场合标明影片中的云南面具戏的艺术元素来自“安顺地戏”。但原审判决中认定,“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这是对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误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3、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段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不仅主观上存在过错,其行为客观上亦已造成误导的实际后果,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亦已提交证据证明误导后果的存在。据此,原审判决中的上述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4、《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在具体使用“安顺地戏”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但却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上述使用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仍坚持原审诉讼中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安顺地戏”并不能够依据《著作权法》享有署名权,涉案电影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并未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同时,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与‘安顺地戏’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其并无资格提起本案诉讼,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因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原审判决在“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诉称”部分有“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这一表述。
原审起诉状中针对被控侵权行为的相应表述为“三被告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中使用了‘安顺地戏’,并把‘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却没有在任何场合进行说明,澄清事实,这种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
庭审中,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著作权法》署名权中的“名”应理解为既包括作者的名称,亦包括作品的名称,本案中则指向的是作品的名称。“安顺地戏”虽是一种剧种,但其亦属于作品,被上诉人在使用时应对该作品名称予以标注,但其并未标注,故其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
上述事实有原审判决、原审起诉状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焦点问题:
一、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可知,民事案件的适格原告应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因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故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只有在与“安顺地戏”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由查明事实可知,“安顺地戏”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由安顺地区的人民世代相传、继承、丰富而成。因这一文化遗产系安顺地区人民共同创作并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并不归属于某个特定民事主体,因此,当他人的使用行为对这一文化遗产造成损害时,难以由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主张权利。
本案中,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虽然并非“安顺地戏”的权利人,但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七条的规定,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在“安顺地戏”已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下,作为“安顺地戏”的管理及保护机关,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有资格代表安顺地区的人民就他人侵害“安顺地戏”的行为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据此,本院认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是否应为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指控的侵权行为系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地戏”错误地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不对其予以澄清的行为,因此,判断张艺谋、张伟平、新画面公司是否应为这一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均有义务对涉案电影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由该规定可知,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享有,制片者有权就电影作品对外行使著作权并获得利益。编剧、导演等民事主体虽享有署名权,但其并非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就电影作品对外行使著作权并获益。虽然《著作权法》中对基于电影作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并无明确规定,但基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相对等的原则,权利人在行使民事权利的同时亦有义务承担基于该权利客体而产生的相应责任,故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作为著作权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亦当然应承担基于该电影作品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据此,本案中,基于涉案电影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涉案电影的制片者,而非编剧、导演等其他民事主体承担。
因《著作权法》中对于作为著作权人的“制片者”在电影作品中的标注形式并无要求,实践中亦存在多种标注方式,故对制片者身份的认定应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予以考虑,而不能仅依据电影作品中的标注形式予以确定。同时应注意的是,《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制片者”并不等同于具体电影作品中标注的“制片”或“制片人”,前者系《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用语,是指对电影作品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后者系电影行业中的用语,二者并非当然是同一主体。
具体到本案,虽然张伟平在涉案电影中标注为“制片人”,但这一标注并不相当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制片者。在涉案电影中标注的出品单位及《电影公映许可证》中载明的出品人均为新画面公司的情况下,结合电影行业的惯例,本院合理认为涉案电影的制片者应为新画面公司,新画面公司对涉案电影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其系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主体。张艺谋仅系涉案电影的编剧、导演,其并非涉案电影的制片者,张伟平亦非涉案电影的制片者,故张艺谋、张伟平均非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主体,不应对被控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三、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涉案电影中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方式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侵犯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安顺地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却未在任何场合对此予以澄清,其行为构成了对“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的侵犯,违反了《著作权法》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署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
对此,本院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著作权法》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侧重于行政保护,《著作权法》则侧重于民事保护,二者具有不同的立法宗旨、保护方式及保护条件。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亦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安顺地戏”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实仅意味着其应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至于其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还要看其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的相应规定。
具体到本案,因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的是“安顺地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署名权,故本案的审理应以《著作权法》中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及署名权的相关规定为法律依据。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一特殊类型的作品,《著作权法》中尚无具体规定,只是在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尚未制定出相关的著作权保护办法。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立足于《著作权法》,故在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关著作权保护办法的情况下,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对其署名权的保护亦不例外。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知,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是“作者”,权利客体是具体的“作品”,权利内容是在作品上标注作者的名称。也就是说,署名权中的“名”指的是权利主体(即作者)的名称,而非权利客体(即作品)的名称,他人只有在使用作品而未署“作者”的名称时,其行为才可能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至于是否标注了“作品”的名称,则并非署名权调整的范围。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将署名权理解为对“作品”名称的标注,这一理解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在此基础上,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的规定,如果本案事实同时符合下述两要件,则可以认定涉案电影中的使用行为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首先,“安顺地戏”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中有关署名权的要求;其次,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属于受《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
对于“安顺地戏”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中有关署名权的要求,本院认为,依据上述规定,只有当“安顺地戏”或者是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即作者),或者是权利客体(即作品)的情况下,其才可能获得《著作权法》署名权的保护。因“安顺地戏”显然并非权利主体(即作者),故本案的判断关键在于其是否构成署名权的权利客体(即作品)。如“安顺地戏”构成作品,则应进一步对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主张的“安顺地戏”这一标注方式是否属于“作者”的署名予以判断。
对于“安顺地戏”是否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本院认为,依据《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只有对思想的具体表达才可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其仅是具有特定特征的戏剧剧目的总称,是对戏剧类别的划分,而非对于具体思想的表达,故“安顺地戏”并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任何人均不能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享有署名权。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安顺地戏”虽是一种剧种,但其亦属于作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其不构成作品,并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故对于“安顺地戏”这一标注方式是否属于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作者”的署名方式这一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本院对此将不予论及。
在此基础上,本院进一步对于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受署名权控制的署名行为予以评述。本院认为,基于与“安顺地戏”相同的理由,涉案电影中对于“云南面具戏”这一名称的使用,亦仅属于对于特定剧种名称的使用,其既非对署名权权利主体(作者)的标注,亦非对权利客体(作品)的标注,故这一使用方式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同时,本院亦认为,涉案电影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使用的艺术元素进行相应虚构,具有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虽涉案电影中实施了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且未对此予以澄清,但鉴于“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其不符合《著作权法》第十条署名权的规定,任何主体无法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享有署名权,且涉案电影中“云南面具戏”这一名称的使用亦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行为,故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上述行为不可能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侵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上述行为侵犯了“安顺地戏”署名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应指出的是,因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明确主张构成作品且享有署名权的是“安顺地戏”,而非其中的“具体剧目”,故本院作出的上述认定仅针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而未涉及其中的“具体剧目”。对于“安顺地戏”中的具体剧目(如涉案电影中使用的《千里走单骑》等剧目),本院认为,因其属于对于思想的具体表达,故可以认定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事主体可以针对具体剧目主张署名权。
四、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中将原审起诉状中表述的“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理解为“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这一理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在原审起诉状中确有“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这一表述,依据上述表述进行字面理解,通常会理解为其主张享有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为“安顺地戏”,但因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而“安顺地戏”显非民事主体,其不可能成为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故上述字面理解显然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亦不符合常理。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考虑到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系作为“安顺地戏”权利人代表提起诉讼这一因素,将上述表述合理理解为“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其虽在表述上有失严谨,但尚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据此,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中认定“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这一认定系对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误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原审诉讼本意的理解来源于其起诉状中的具体文字表述,起诉状中对于被控侵权行为的表述主要为“三被告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中使用了‘安顺地戏’并把‘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却没有在任何场合进行说明,澄清事实,这种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本院认为,起诉状中上述文字表述可以合理理解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涉案电影中将“安顺地戏”称之为“云南面具戏”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仅是要求“被上诉人保留影片原有画外音的情况下,在片尾或其他场合标明影片中的云南面具戏的艺术元素来自安顺地戏”这一含义仅从上述文字表述中无法当然得知,据此,原审法院基于其对原审起诉状的理解,对于“涉案电影《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是否违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予以认定,并未违反上诉人原审起诉状中所体现出的意思表示,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所使用‘安顺地戏’片段虽根据剧情称为‘云南面具戏’,被告在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从整体情况看,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者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为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故原审法院应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在“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的情况下,其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从《著作权法》角度进行判断,被上诉人对于“安顺地戏”的使用行为其主观并无过错,客观上亦未对著作权本身造成损害后果。据此,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无误,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在认定影片《千里走单骑》在具体使用“安顺地戏”时,就戏剧表演的配器及舞台形式加以一定的改动的情况下,却未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上述使用行为构成对其署名权的侵犯,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依据上述规定,只有他人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的系“已有作品”的情况下,才需要经过原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鉴于本院已认定“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不构成作品,并非《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故上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审判决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涉案电影中的使用行为构成侵权,其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著作权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七百五十元,均由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免责声明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交流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更不作为营利使用。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作删除处理。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著作权等权利问题,请相关权利人根据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在两周内速来电、来函与智豪团队联系,本网承诺会及时删除处理。来电请拨打02363891336、13310240199。
- 相关阅读:
- · 被告人甘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
- · 被告人霍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
- · 被告人李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 · 被告人黄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
- · 被告人徐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我们的团队
更多>>
首席律师动态

亲办案例
查看更多罪名亲办案例
zhihaolawyer

微信号:zhihaolawyer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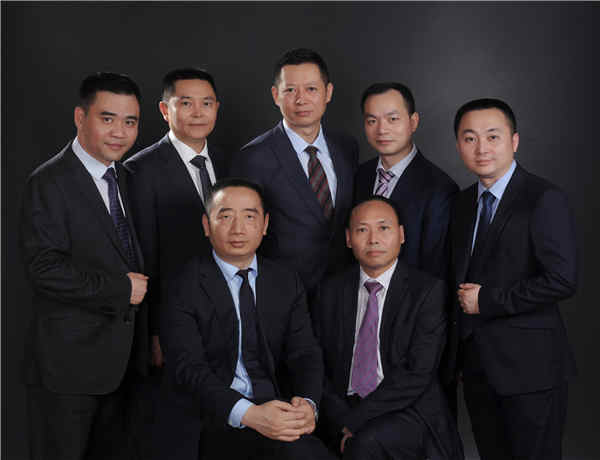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